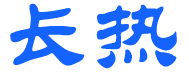电影剧本:那一个有沙尘暴的春天(二)
(3)、玉洁家
玉洁心事沉重地推开门进家。
刘庆正靠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宰相刘罗锅》的片尾曲响着。
豆豆听到开门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脸上带着不悦和委屈。
玉洁和豆豆的目光对视着——
玉洁:“怎么了?豆豆,发生什么事了吗?”
豆豆不说话,从眼睛里留下两行眼泪。
玉洁焦急地:“到底怎么了?”她走上前替女儿整理着略显凌乱的头发。
刘庆关上电视机,把手里遥控器顺手丢到沙发上,站起身来,愤懑不平地:“这叫什么事啊!想整人家法轮功,连小孩子都得逼着跟着叫好。凭什么非得表态不可?!我就不信这个邪,豆豆,明天我找你们校长去!他们敢开除你!”
玉洁惊诧不已:“开除?不表态就要开除?!这是哪家的王法?!”
“老师是这么说的。” 豆豆委屈不堪地边说边流泪。
刘庆:“得,别哭了豆豆,明天我就找你们老师去。天太晚了,快去洗洗睡觉吧,明天还得上学呢。”
豆豆看着妈妈——
玉洁叹了口气,问道:“作业都做完了?”
豆豆点了点头。
玉洁捧起豆豆的脸,“看你,哭得眼睛都肿了。好了,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去洗洗脸,把牙刷了,睡觉去吧,啊。”
豆豆乖乖地走向洗漱间,客厅里片刻宁静。
刘庆侧过脸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玉洁也抬起头看了看。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玉洁有些报歉地说:“对不起,今天回来太晚了。”
刘庆:“我说啊,你这个班主任就别干了,咱家也不缺你那点班主任费,弄得早出晚归的。”刘庆说着,看着玉洁的脸色,“你今天怎么啦?看你进门就显得不顺心,谁又惹你生气了?”
玉洁不想解释太多,只是简单地说:“一个学生的事,也牵涉到法轮功。我已经处理过了。”
刘庆发起感慨:“唉——我就纳了闷儿了,现在整法轮功都整到学校里啦,我怎么觉得跟活在68、69年似的!”
玉洁没说话,脱下外衣,连同挎包一起挂到衣架上,表情沉重。
刘庆看到玉洁有心事,改换了口气:“赶紧洗洗吃饭吧,看咱家这个班主任的谱儿有多大,当经理的亲自给你下厨掌勺。”说着走进厨房,端上饭菜。
豆豆走出洗漱间:“爸爸妈妈,我睡了啊。”
玉洁:“哎,快去睡吧。”
豆豆进了自己的卧房,轻轻关上了房门。
玉洁在洗漱间洗了一把脸,用毛巾擦拭干净,走出来,到餐桌前坐下来。
对着桌上挺丰盛的饭菜,看看刘庆,略表歉意地笑笑,端起碗慢慢吃着,心事沉重。
刘庆坐在一旁看着玉洁:“又是什么烦心的事,说出来,帮你破解破解。一看你这表情,估计你这回是真的遇到难题了,不会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吧?”
玉洁叹口气:“我现在是真的越来越搞不明白了。你说如今这当官儿的是怎么的了?现在中国的破烂事还少吗?国企破产、工人下岗、农民没饭吃、社会治安恶劣、社会道德沦丧,天灾人祸不断,放着这些关系到国家兴亡、百姓生计的大事不管,却动用全部力量去对付一个法轮功,你说江泽民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呀?”
刘庆:“你算问着了,人家不是说过么,江泽民的脑子就是有毛病呀,”刘庆降低声调,凑近玉洁,“他其实是个蛤蟆精!”
玉洁:“你别在这儿瞎打哈哈!”
刘庆一付认真样:“没打哈哈,人家真是这么说的!”
玉洁:“那些炼法轮功的人也让人搞不懂,要炼功就在家里好好炼嘛,到北京上什么访呢,说要讲真相。哎,共产党搞了七、八十年,什么时候让人说过真话,什么时候让老百姓知道过真相呀!”
刘庆:“其实这事不是明摆着嘛!共产党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权嘛!共产党从建党那一天起,内斗外斗,斗了几十年,死了多少人,不就是围绕着一个权字嘛。要么怎么人家说,共产党是趟着人血走过来的。法轮功炼来炼去,人越炼越多,都炼到中南海外边去了,那个江泽民小肚鸡肠,都快吓死了!你想,他能跟法轮功和平共处嘛?”
玉洁:“法轮功跟政治根本就没关系!炼法轮功的咱身边有多少啊,豆豆她奶奶不是也炼吗?十六号的秦老师一家都在炼法轮功,你看他们都象要夺共产党的权吗?”
玉洁挟起一筷子菜放到嘴里,“这些人炼功不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嘛,这对国家不是个好事吗?说炼法轮功的人搞政治,我看全是让他们给逼的,小鸡你要是追急了,它还会飞上墙呢,何况成千上万的人哪!”
刘庆打开冰箱倒了杯饮料,喝了一口,又坐到桌旁:“嘿,让你说着了。这共产党要是好,它在国际社会上能那么孤立吗!当年‘六.四’的时候,咱对共产党不也是一腔热情吗?以为是帮助咱们的这个党揪腐败、促进廉政建设,可到头怎么样,十几万精锐部队,坦克、大炮沿着长安街长驱直入啊,热血青年被打死、碾死了多少!说中国历史上对学生最狠的北洋政府的段祺瑞,也不过才开枪打死了二十七个大学生。你说这共产党有多坏,有多邪性吧!”
玉洁皱紧眉头,叹了口气,放下碗筷:“我有个学生,叫张小欧。学习挺不错的,过去一直是我那个班的班长、语文课代表。他的爸爸妈妈都炼法轮功,结果一个被抓起来关进了劳教所,一个被通缉,出走在外。唉,现在孩子只能放到奶奶家,也没人照顾。”
玉洁眼里透出一丝哀婉。
沉顿了片刻,玉洁把眼光挪到了刘庆身上,“今天,学校又来一帮教育电视台的记者,硬要拍个什么纪录片,把孩子失学的责任硬加到炼法轮功身上,你说,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
刘庆:“现在政府说什么,谁还当真啊!我要是对这个政府还有一点信心和热情,也不会好端端的一个政府官职不要了,下海去瞎扑腾呀。你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往心里去不就得了!”
玉洁又叹口气,窝心地嘟囔道:“好了,不说了,一说这些破烂事就让人生气。”她迅速地端起饭碗,把剩下的一点饭菜拨到嘴里,“都这么晚了,快收拾收拾睡觉吧。”
(4)、夜,玉洁的卧室
玉洁睡不着,她翻了一个身。
身旁的刘庆已经发出轻微的鼾声。
玉洁睁着眼睛,想着心事。
她轻轻叹口气,又翻了一个身。
她就这样眼睛一眨不眨地想着心事,好久。
她轻轻探起身来看看睡在身边的刘庆,刘庆睡得很沉。
玉洁小心翼翼地坐起来,下了地,摸黑走出房间。
玉洁来到洗漱间。
轻轻地拧开了水龙头,她把两手浸湿了,在脸上沾了沾,用毛巾轻轻地拭着。
她对着镜子,静静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然后关了洗漱间的灯,轻轻来到书房。
书房的书柜上有一幅玉洁和母亲的合影——
那时的玉洁,高中毕业,清丽活泼,她揽着妈妈开心地笑着。
妈妈的脸上充满了慈祥。
玉洁轻轻地拂拭着像框,看着相片中的妈妈。
(玉洁回忆)
到处是红旗的海洋,人头攒动。
宣传车在人群中穿行。
一些脖子上挂了大牌子的人被红卫兵揪斗着游行。
一些红卫兵正从一间房子里往外搬各种各样的书籍往火堆里扔。
熊熊的火焰腾空而起,黑烟缭绕。
周围满是看热闹的人群。
透过闪动的火光,人群的脸被不断地扭曲着……
少年玉洁——
惊恐的眼睛。
她正趴在窗户上往外望。
黑压压的红卫兵正从外面冲向她家的楼房。
一个接一个沿着楼梯跑动的人脚,木楼梯“咚、咚、咚”被震动的声音……
小玉洁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在颤抖。
妈妈在床上撑起身子。
冲进门的红卫兵们象凶神恶煞一样围住了玉洁的妈妈。
他们把她从床上拖了下来,从木楼梯上一路拖下去。
小玉洁大声地呼喊着,从后面追过去——
站立不稳,小玉洁从木楼梯上滚了下来。
她慢慢爬起来时——妈妈已经被拖走了。
小玉洁额角流着血,伏在地上痛哭不止……
妈妈头发凌乱地被围在一群人中间,她带着祈求的目光对人们说:“你们相信我,我没做过坏事……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
只听一个人冷冷地说:“得得得,你也甭解释,党说你是啥,你就是啥。”
另一个冷冷的声音:“就是,是你英明,还是党英明,啊?”
围着的人群哄笑着散去。
妈妈呆呆地愣在那里,无助、失神的双眼望着昏暗的天空……
小学校的门打开了——
放学的孩子们熙熙攘攘、说说闹闹涌出校门。
小玉洁背着小书包,沿着围墙往家走。
几个顽皮的小男孩,追上她,尾随着她,又围上她,一阵笑骂:“狗崽子!你妈是反革命。”“她是小反革命!”
“那天我看见她妈还在街上跟人说她不是反革命呢,她妈现在是精神病。”
“对,是反革命加精神病。”
小玉洁把头埋在怀里,眼里流着无辜的泪。
一个教师模样的老先生走过来,“你们干什么欺负人?你们老师是谁?我找你们老师去!”
几个男孩子一哄而散,跑得不见了人影。
老先生用手抚摸着小玉洁的头。
小玉洁抬起满含眼泪的小脸,抽泣着望着老先生。
老先生柔缓地说:“孩子,快回家吧。”
小玉洁点了点头,往家的方向跑走了。
老先生带着怜惜的目光看着小玉洁跑走的方向,叹着气摇了摇头……
阴沉沉的天,一阵阴风吹过,下起了雨。
小玉洁拎着装有十几个鸡蛋的破旧小篓小心地往家走——
忽然一个人疾步走过来,朝着路上的人们大叫着:“哎呀,吓死我了!那边有人跳楼了!说是个反革命。哎呀,吓死我了……”
街上的人们朝着那人指的方向奔跑过去。
浑身淋湿的小玉洁惊恐万状。
她下意识地丢下手里的鸡蛋篓,呆呆地愣在那里。
地上小篓里的鸡蛋破碎了。
小玉洁似乎突然清醒了,她拼命地往家里奔跑,雨水顺着头发滚到脸上,地上的泥水溅到身上——
“砰——”,房门被猛地推开,浑身泥水的小玉洁惊恐地站在门口。
妈妈无力地从床上探起头来,怜爱地望着她:“玉洁,买回来啦?哎呦,你淋成这个样子,快换上干净衣服。”她努力从床上挣扎起来。
小玉洁大哭着扑到妈妈怀里:“妈妈——我以为那个跳楼的是您呢,妈妈——您可别死啊——您别死啊——”
妈妈先是一愣,而后紧紧搂着女儿,悲声恸肺:“玉洁,妈妈不死,妈妈跟你好好活着——我们好好活着——”
母女俩抱头痛哭……
(回忆结束)
像框里母亲在慈祥地微笑。
(玉洁画外音)“文革过去了,妈妈的冤案终于平反了。可是文革带给妈妈的身心交瘁和满身病痛,却使妈妈在平反的第二年永远离开了我。”
玉洁手里捧着像框,从回忆中清醒过来。
她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将像框放回原来的位置,小心地摆正。
她转过身来到窗前——
轻轻揭开窗帘向外面看。
外面月光皎洁。
玉洁静思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
她关掉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