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劳教所和冤狱迫害 安徽冯燕女士控告江泽民
修炼法轮功,人们按真善忍做人,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九年间,在华夏大地曾经得到广大人民的普及,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之心以其最高领导人地位,凌驾于宪法之上,一九九九年七月悍然在中华大地发起了迫害法轮功运动。他在高层领导的信件和讲话形成了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成为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和纲领。
江泽民亲自建立了迫害指挥系统,通过中共内部各级建立“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和“610”办公室,直接操控各级官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驱动喉舌媒体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二零一五年,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了“有案必立”的公告后,冯燕于当年六月二十五日,向两高投递《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在《刑事控告状》中,冯燕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却因信仰法轮功、讲真相被五次非法关押和刑罚。”在二零零零年,在精神病院遭迫害,医院“用高压电棍对着太阳穴电击,电棍啪啪的冒着蓝火,我被电击的头晕目眩。”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
二零零六年,在合肥女子劳教所,“‘帮教团’的三个人对我暴打,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头上、脸上,用四条腿的小凳子砸我的腿,又把我按在地上坐着,两个人站在我的两条腿上用力跺,我被打的鼻青脸肿,头肿的象气球,眼象熊猫眼,嘴唇肿的合不上,头上的疙瘩一个挨一个……”
 拳打脚踢 |
下面是冯燕女士在《刑事控告状》叙述的她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
我是一九九六年底学炼法轮功的,炼功后原来的关节炎、肩周炎、坐骨神经痛、腰痛病等都好了。法轮功还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事事处处用这三个字对照自己的言行,使家庭和睦,道德回升,我对法轮功给我及家人带来的美好,感激之心无法用语言表达。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对我们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后,公安、警察一次次抄家、绑架,我的母亲、婆婆、丈夫及几岁的孩子惊恐万分、终日惶惶不得安宁,特别是我几岁的孩子精神受到的伤害更大,丈夫因承受不住,导致家庭破裂。
进京上访遭绑架、勒索
一九九九年皇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与姐姐去北京上访时,才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当晚就用车把我们拉到安徽驻京办事处,三天后,被颍上县公安局政保科的张培强、颍上县水利局常其景与县里一位干部用手铐把我与姐姐铐在一起,带到颍上看守所非法关押。
我们尊重政府,相信政府才行使一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后,又转拘留所,临离开看守所时,我要我的三百多元钱,看守所常所长说:“钱作废了!”就是不给。在拘留所,一直关到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才回到家中。离开拘留所时,又勒索了近千元钱,否则就不放人。
在精神病院被电击和吃损害神经的药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日,颍上龙门派出所片警陈满春又把我抓到拘留所关押,说是怕我再上访。我绝食抵制迫害,二十四天后,颍上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杨忠成、张培强等人把我送到阜阳精神病院迫害,在精神病院遭到野蛮灌食、按倒在床上,用高压电棍对着太阳穴电击,电棍啪啪的冒着蓝火,我被电击的头晕目眩;还被绑在床上打点滴、逼迫吃精神病药,特别是精神病药对我身体伤害很严重;大脑迟钝、全身发软、背部发酸、心发急、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心跳过速、呼吸急促、感觉要死了。就这样,日日夜夜摧残我三十六天后,才放我回家。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
在派出所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颍上龙门派出所片警陈满春深夜带一帮人到我家,敲门砸门,又喊又叫,借查户口为名叫我开门,我深知他们的诡计,不开!他们就一起推门撞门,结果门锁抵不住,被撞坏,一帮人破门而入,把我绑架到龙门派出所,对了笔迹,按了手印,才放我回家。
在合肥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一年的九月份,我被绑架到拘留所,我因坚持信仰真、善、忍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劳教二年。二零零二年五月份,我被送进合肥女子劳教所,遭到劳教所惨无人道的迫害。
二大队的邓大队长,还有叫林云的队长,安排我与两个包夹单独住小号,强行对我实施洗脑,她们当我面骂法轮功、骂师父、撕法轮功师父的像,体罚我站着,每天要站十几小时,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不让与别人说话、不让洗漱、洗澡、不让去食堂吃饭,最热的伏天,两个星期才允许我洗了两次澡,导致全身发馊、发臭,走到哪就臭到哪,她们实在被熏得受不了,才允许我洗一次澡,还有一次,五天五夜不给我睡觉,历经了三个月的日日夜夜迫害后,于二零零二年九月份被转到三大队。
 中共酷刑示意图:铐在床架上 |
一到三大队,指导员马丰平和队长陈杰,因我不配合劳动亲自将我两臂铐在监室铁架双人床上成“十”字形站立,从凌晨四点一直站到深夜零点,两腿站的红肿、疼痛难忍,两臂被架的又痛又酸、头晕目眩,五天后,又被按在地上强行灌食,又强行给我穿上了“约束衣”。就这样断断续续被迫害了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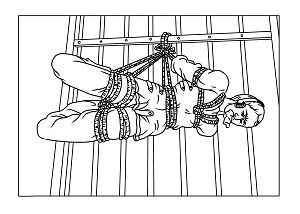 中共酷刑演示图:约束衣 |
二零零三年九月,因我不配合穿囚服,队长陈杰又指使普教人员把我绑在小号双层铁架床上,成“十”字形站立,直到休克才放下来。后来,又把我双手反铐在床头上,双脚绑在床的另一头上,中间用绳子把小肚部位固定在床上,不能吃饭就强行灌食,不能侧身,更无法翻身,无法大小便,脊背溃烂,屋里腥臭无比,摧残了十五个日日夜夜。然后就让我躺光板床近一个月,整夜整夜我都睡不了觉,因为睡着会被冻醒的,直到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中旬才回号房。
 中共酷刑示意图:长期捆绑在床上 |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大队马丰平直接把我交给二大队邓大,邓大和劳教所的潘姓所长借口叫我背《所规队纪》,把我双手背铐拖到禁闭室,叫来四个犯人连同合肥市“帮教团”的三个人对我暴打,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头上、脸上,用四条腿的小凳子砸我的腿,又把我按在地上坐着,两个人站在我的两条腿上用力跺,我被打的鼻青脸肿,头肿的象气球,眼象熊猫眼,嘴唇肿的合不上,头上的疙瘩一个挨一个,两腿肿的套不上裤子,两脚肿的穿不上鞋,遍体鳞伤,全身无处不痛。至今我左腿还有一个大硬块,并被延期关押十个月。
经过这三十四个月人间地狱般生活,我九死一生,于二零零四年八月份,才离开这人间地狱——合肥女子劳教所。可家已破碎,无家可归,只好回到母亲身边,至今劳教释放证书还被扣在颍上县公安局杨忠成手里。
在宿州市女子监狱遭暴打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份,一个深夜,我和儿子正熟睡,我被敲门声惊醒,我没开门,凌晨五点钟左右,我去厕所,路过正对我家院门的面包车,我近看里面睡两个人,我直接从厕所旁边翻墙头跑了,从此流离失所。当时,十二岁的孩子还睡着,我无法想象孩子将面临的处境。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我与同修去博林学校看儿子和讲真相时,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太和看守所,分管迫害我的警察闫民,为阻止我炼功,三次给我戴拐棍镣(脚镣、手铐中间用一尺长的铁棍连着),戴上它:站不直、伸不直、无法换衣、无法洗澡、无法大小便。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我被送进宿州市女子监狱,在那里三人“互监组”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言谈举止必须服从“互监组”。哪怕使个眼神,都会招来一顿打骂。每天还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劳动十六至十八个小时,身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在那样的环境中,还强行给我洗脑,警察徐队长和靖教利用邪悟的人轮番上阵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真是度日如年。历经六十个月的牢狱生活,终于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才回到母亲身边。
“610”要挟 在生活上迫害
二零一一年,我申请到一套廉租房,这时县610主任周阳春和团结社区顾杰等到我家来,要我写“保证不炼法轮功”了,才给我廉租房钥匙,否则就不给我钥匙,我说我修真善忍,不说假话。我按真善忍做好人,炼功身体好没有错。610越权拿走钥匙,扣着不给。
二零一二年母亲住处要拆迁,母亲因老年人租不到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要分给我的廉租房,二零一四年,我和母亲才住上廉租房。



